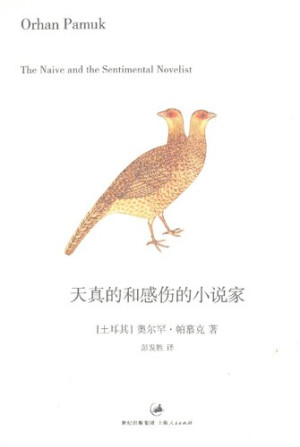一
我探身出去,踏过浸没脚踝的积雪,今晚的圆月如冰球般剔透闪耀,将光辉洒下这个县城里的每一栋小小建筑,而我寄宿在这庞大的机械怪物中。
只有这里,粗大的金属管道笔直地交织,扶梯与楼梯如同粘在这些管道间随处可见,管道的尽头矗立着规整的烟囱口,它们一同构建出来自20世纪60年代规整的工业美学。
在这里工作的爸爸和我讲过,这里叫钢铁厂,同样也是一个个房子。
但我不理解,触摸家里的墙壁,我可以感受到砖块的粗糙;触摸院子的土墙,我可以感受到尘土的细微夹杂着稻草的反抗;但触摸这个钢铁厂,留在手里的只有金属的冰凉,和糊满手心的铁锈与煤粉。
我怀念家里,一点攀爬的技巧加上一根木头桩,我就可以坐在平房房顶上最喜爱的角落,张望鳞次栉比、同样低矮的房屋,那才是房子本来的模样。
如今这样的房子就摆在我面前,只需走完这条唯一且宽广的,连接着工业与生活的泥土路。但对我来说,狭隘的岩石路更加充满温度,它留存在去年春天的公园之旅。
二
难得的,我们一家子有了去大城市转一转的机会。
曙光初现,在车站旁广场暂留的人已睡醒消失,小镇的交通系统重新恢复了工作。回头望去,刚刚发动不久的火车,驾着黑与白交融的迷雾,将那矮小的二层火车站遗弃在朝阳的光辉中。
火车上的几个小时,各式各样的人穿梭在我稳稳当当坐着的硬座旁的过道,好像并没有安静过片刻,但满怀好奇的我并不需要这份安静。
在过道的另一侧是个三十几岁的妇女,正聚精会神地读书,而且是真的在“读”书,操着我熟悉的浓重的东北口音,一个字又一个字地念着,但她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大家的嘈杂中。
我不知道她能否听得清自己的声音,但看得出她很满足,仿佛整个世界纯然构成在她口中的词语。但让我注意到她的并不是那看书的举动,而是身上我从未见过的红色碎花衫,让我知道衣服除了灰色绿色深蓝色,还能如此漂亮。
落日余晖下,不久后火车也将抵达终点。早已饥肠辘辘的我津津有味啃着两分钱一个的粗粮馒头,直到那妇女掏出一件包裹。十字扎紧的红绳下,灰黑的报纸隐约透出一小块油渍,浸染在“人民日报”四个字上。
将报纸一层层展平,露出码放整齐的酥饼,金黄发光的外皮上点着几粒黑芝麻,每一个酥饼的大小完美一致。我确信这酥饼香甜的味道,一定穿过人群制造的浑浊气息,冲击进我的鼻腔,所制造出的迷人幻觉让我肚子里的馒头飞速消化。
我还是好饿啊!之后我的脑中只剩下酥饼。
三
这处公园并没有像样的一个大门,公园与街道的毗邻制造出一种开放感,让我感到十分亲近。跨过一段只是装饰的小桥,白丁香花朵在树梢紧致地攥成一团又一团,仿佛盛春中降下一场大雪。
在已年久的砖石路的侧面,有一条不知通向何处的小路,烈日当空的正午,两侧的柏树难得地笼罩出沁人心脾的荫蔽。这条小路铺路用的都是整块的岩石,瓦楞纸般的花纹被白色溅射状的斑点所装饰。零落在两侧,来自去年秋季的枯叶还未完全腐败,漂浮着一种我无法描述的气息。
继续低头散步,那些斑点越发地显眼,不禁让我思考是谁装饰出如此路面。这样好的庇荫处,却意外地见不到有谁经过,这些疑问令我略微陷入一种迷惑与不安。
不过老天爷喜欢解答孩子们的好奇,当我再次向天空张望,一滩白色糊状物从天而降,不偏不倚地击中我左侧的脸颊,与此同时的上空,几只鸟类平静地从两棵树的枝头掠过。所有的疑惑伴随着一团怒火的升起得以解答。
狼狈地原路返回,冲洗脸庞的我身边,爸爸和妈妈笑得放肆。
四
湖边,并不辽阔的水面弥漫着微微的绿藻气息,此处一个老爷爷引起我的注意。
老爷爷头发有一半已花白,但昂首挺胸与笔直的腰板俨然不是个向年龄屈服的老人。身穿朴素但材质坚实的黑色长袖长裤,套着一层四处都有口袋的土黄色马甲,头上戴着竹篾编织的草帽。如果他提着一套鱼竿和红色塑料桶,我毫不犹豫地相信他来这里是为了钓鱼。
只不过他身旁是一个和他几乎一样高的大家伙,一层又一层嵌套的乳白色圆柱体指向湖面对岸树林的最高处,几根支撑它们的黑色铁棍构成精致的三角形。铁棍旁的纸板上用墨汁书写了几行用于说明的小字,小字上方“公益鸟类观测”几个大字显眼又鲜艳。
这样独特的场景肯定不仅只有我注意到,同样走向那个老爷爷的还有另外的一家三口。这家人更像是知识分子家庭,身着规整中山装的男人戴着圆形镜片的黑框眼镜,白底红色栅格裙子的女人理着整齐的短发。
而那个穿着也许是她奶奶亲手编织的布衣的女孩应该比我年长两三岁,大概刚满十一二岁,此刻怀揣着不输于我的强烈好奇心下,站着小凳子,把头探向镜头,在这陷入痴迷的半分钟里惊讶地张着小嘴,之后洋溢着满足的笑容,牵着父母的双手蹦蹦跳跳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
几分钟后我迫不及待地登上那个小板凳,但透过目镜只看到了一片漆黑。
“你个娃凑近一点看喜鹊嘛!”这老爷爷不算亲近也不算冷漠,但声音洪亮得如同那笔直的腰板。
凑近后,映入眼帘的是两只鸟在同一枝头休憩,一只鸟对望着另一只鸟,直觉告诉着我刚刚的好事就是这两个家伙干的,但很快这股窝火就消散掉。我未曾想过,通过这个大家伙,可以如此清晰安静地观赏鸟类,而眼前的喜鹊实在生动。
虽为喜鹊,但神情却并无几分喜色,更像是在耍酷。纯净的白羽和黑羽两侧,唯有双翼的末端泛着一丝幽秘的蓝光。
无奈这大家伙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地方,突然其中一只离去,只有起身那一瞬映射入眼,留下一道黑色的弧线,还有微微颤动的树杈。
五
路灯下,一片雪花旋转,舞动,最后沉睡在我早已通红的鼻尖,与之而来的微凉将我从幻想中拉回。
不知不觉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吗?这一排排整齐的平房,像极了家里那一排排,只是这里唯独没有容许我的一间。摆在面前的这一面墙,是用白色油漆粉刷的经典语录,虽然略微褪色,但每个字仍然方正。
机械怪物仍然放射着咄咄逼人的寒光,但早已在远方汇聚成一点,淹没在数不清的雪花浪潮中,正如彼时消失的火车站一般。
一股强烈的脱力感袭来,这种虚弱感如同我四岁时那次高烧,我大口地喘着虚气。
再也走不动了,我趔趄地倒向那面墙壁,好在后背坚实地靠在上面,但身体还是随着双腿无力的支撑而滑下,蹲坐在灰尘与化雪混杂着的泥土路上。对面人家,一条守在门口的老黄狗蜷缩成一团,却安逸地沉睡在栅栏状的铁门旁。
但心灵可以创造出抵御寒冷的温暖。
“小孩子,大晚上不回家在这做什么?”不远处传来一个青年男人的声音,看来是有人发现我了。
努力睁开疲惫的双眼,凑上前的男人身穿一身军绿色的棉袄,厚实的帽子中央是一颗鲜红的五角星,五官端正,活像从电影里走出来的还乡的解放军。此刻他向我递来随身的水壶,温和地说:
“我带你回家吧。”
冰球般的圆月下雪花依旧狂舞,山峰间的荒漠中央是一条早已被人踏出的宽广的泥土路,路上只有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但他们并不孤独。大人背着小孩,微笑着倾听小孩讲的故事;小孩身披棉袄,那是他穿过最温暖的衣服。
六
熟悉的床帘内,肌肤的触感所传达的温热一直持续到被窝。手机屏幕上或是八点或是九点已不值得在意,我将目光停滞在遥远又亲切的4月21号。
“生日快乐。”我如是说道。